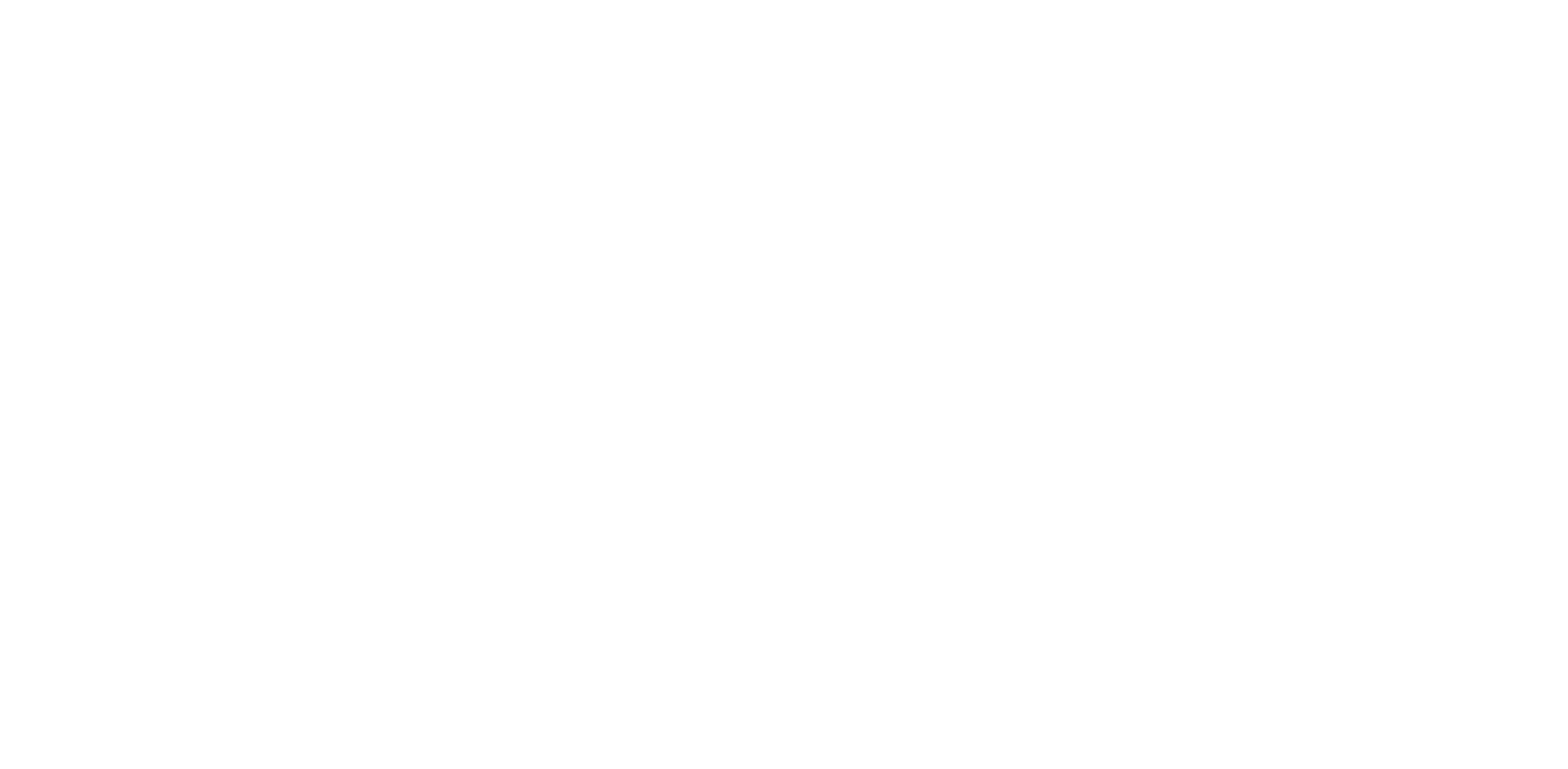【人物简介】
徐一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上海市重性精神病重点实验室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精神卫生学系主任、复旦大学精神卫生研究院院长、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主任。2003年抗击SARS期间,他是本市首位进驻传染病医院的精神科专家。

抗疫战进入关键期,除了直面病魔的患者与奋战一线的医护人员,全社会都被疫情的点滴变化牵动着情绪。爆炸式的信息从手机、电脑涌入我们的生活,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惧、对未知的焦灼、对负面新闻的愤怒、对不幸故事的哀伤……难以纾解的情绪困扰,也像“慢性病毒”侵蚀着我们的内心。当下,我们需要怎样的心理支持?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身处疫情的非常时期,从宅家到复工,有不少市民慢慢感觉“心态有点崩了”。为了减少交叉感染的危险性,面对面交流疏导或许不是目前的最好方法。能否请您全面介绍一下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推出的咨询渠道?
徐一峰:第一,市民可以拨打心理援助热线,除了市级层面的12320-5以外,我们还整合了各区专业力量,专门开设1+17(本市17个区县精神卫生机构,与各区目前行政区划稍有不同)战疫心理专线021-55369173,全天24小时开放。其实心理援助热线在全年长期开通,但目前,每天我们可以接到约50个电话,较平时数量翻了一番。
第二,中心官方微信号开设互联网快速问诊平台,提供在线心理测评和专科问诊服务,市民关注后可进行免费咨询,1月30日开通至今,已累计回答问题3000余个。
第三,市民可登录上海健康云公众服务平台,进入心理健康板块,针对心理困惑在线接受专业咨询。目前,后台显示线上心理自我评估问卷完成人数超过6万,可见市民的需求量还是很大的。
除此之外,从1月30日起,中心还有40名专家自愿支援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心心语”心理热线027-85844666,每天也可以接到约30个电话。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这些“云咨询”的市民们,主要碰到的心理困惑是什么呢?
徐一峰:我们总结了一下,主要是7大方面:一是询问疫情防控知识;二是有轻微咳嗽等症状者怀疑自己已经疾病缠身,非常恐惧;三是过度焦虑,担心新冠肺炎随时降临在他身上,有时候还会控制不住发脾气;四是感觉无力、疲劳、食欲减退,已到院检查但依旧坚持自己可能是疑似患者;五是抑郁、想哭,对生活失去信心;六是入睡困难、失眠或睡眠时间短;七是强迫行为,如反复洗手,反复回想自己出门有没有可能被感染,反复想象被感染后的严重后果无法自拔。
但是,真正属于精神疾病患者的极为少见,大多数是出现了应激反应的普通市民。需要注意的是,热线及网络平台都不可以提供干预治疗,只能提供咨询建议,如果经接线医师评估,心理状况已达到异常障碍的市民还是需要尽快到院就诊。为此,我们也开设了特殊时期的心理门诊,为这部分患者提供及时干预。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之前在对发热咨询平台的采访中我们了解到,从数据来看,半夜里打来电话表达焦虑情绪的很多都是女性,这有什么科学依据可以解释吗?
徐一峰:2年前,《自然》曾刊发论文:为何遇到复杂、受挫的事件时,女性能更坚强、更有韧性?文章回顾了1845年至1850年间的爱尔兰马铃薯饥荒,期间男性预期寿命缩短幅度明显大于女性。这是为什么?
第一,虽然男女性大脑构造相似,但回路不同,男性更倾向运动功能、方向感掌控,女性则擅长图像认知、社交功能。第二,女性更容易产生情感性流泪,泪液中含有蛋白质、锰元素及催乳素——排出后对缓解情绪有很大帮助。第三,从现实生活来看,女性较男性有更密切的社会关系网,她们喜欢寻求帮助,同时也能得到帮助,有时“啰嗦”但对健康有益。
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也希望男性在遇到心理危机时能更主动地表达,或许一个电话、一条回复,就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宽慰。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17年前,您是上海第一个进入传染病医院为医患提供心理干预的专家,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呈现出的心理问题,和SARS有什么异同之处?
徐一峰:当年全市仅8例确诊的SARS患者,死亡1例,是一名老先生。当时我进驻传染病医院后,第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为他的爱人、同为SARS患者的老太太提供心理治疗。她说的话我至今还记得,“他是因为我才没的,是我对不起他,我活着也没有意义了。”她戴着呼吸机,说话断断续续;我戴着口罩,也难以长时间交流,因此直接能触到内心的支持性语言就显得非常重要。我告诉她,我们理解、认同你的悲痛,但也要把自责的情绪卸下来,看到生命的美好,“如果您先生还在,他也希望你能有勇气,带着他一起活下去。”
我想,这个案例至今依旧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新冠肺炎在沪的传播性、影响力都远远高于SARS时期,不少患者的自责情绪或成为在治疗中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同样地,医护人员也会产生自责:如果我用了另外一种治疗方式,患者是不是不会走向死亡?
可以说,现阶段精神卫生医师更应该提供的是紧急的支持性治疗,表明“我们和你在一起”。但必须未雨绸缪地对医护人员、患者乃至社会大众提供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心理干预渠道。2003年,北京的许多医护人员在疫情结束后产生了抑郁、焦虑、恐惧和挫折等情绪,我们希望悲剧不要在武汉重演。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其实,许多市民目前也都正在努力走出疫情在心中的阴霾,但似乎很容易受到过载信息的影响,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徐一峰:我们要明确,对于未知的新病毒,没有人是权威。这意味着对非医学背景的普通市民而言,若每天过度关注真假难判的信息、谣言、辟谣与反转,的确容易陷入负面情绪。我的建议是,每天应限制接受信息的时间,就像预防游戏成瘾一样——即便是益智游戏,也应控制分寸。比如,每天为自己设置两三次阅读新闻的时间段,除此之外,阅读、音乐、游戏等都可以带来舒缓。
不瞒你说,我最近就在研究菜谱,也会和家人畅谈疫情结束后的旅行或生活计划。超前性的远景目标,会成为支撑度过艰难时期的重要依靠。除此之外,可以通过在家的运动、肌肉放松、呼吸训练等快速调节紧张、焦虑状态。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除了专业的精神卫生机构,您觉得其他社会部门组织可以在心理干预工作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徐一峰:这一次,上海的社区工作成果大家有目共睹,“守门人”构筑了严密屏障,也把好了疫情防控的第一道关。近年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医生纷纷也将辖区内居民的精神卫生健康纳入管理范畴,但接触的大多属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我想,在疫情当下,大量的居民需求并非来自患者,而是大众情绪需要疏导,如果全科医生和街道居委工作人员、业主委员会等形成联动枢纽,可以为他们指明一条寻求帮助的路径。比如,将心理援助热线信息印成单页,为不上网的老年居民也提供及时帮助。
同时,也有专家提出,此次似乎没有听到太多来自高校心理卫生学界的声音,但由于新冠肺炎是传染病,我们也呼吁没有医学背景的心理学专家和精神卫生科学界联手,将理论结合实际。此外,高校心理学专家也可以结合大学生等青年群体,传播更活泼、平等、友好的心理干预知识。
去年,“健康中国”“健康上海”战略中都将心理健康促进行动纳入了重要举措。我想,经历此次疫情后,我们的公共卫生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与健康促进教育机构应该更好地肩负起保障、科普的责任,让“大健康”理念真正落到实处。
原文链接:徐一峰:给自己一些疫情结束后的盼头,男性也要学习女性“多表达”__凤凰网 (ifeng.com)